2023年度普利茲克建筑獎
他是一位多產的建筑師,設計風格微妙而有力,低調而優雅,以“惜墨如金”的筆觸表達對歷史和文化的敬畏、對現存建筑和自然環境的尊重。通過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現代設計,無論是新建,還是翻新和修復的建筑,他對建筑的功能性和易用性進行了重新構想,并籍此應對氣候危機、改善社會關系并振興城市的發展。
“獲得這一殊榮,能與那些曾經為建筑領域帶來無數靈感的歷屆獲獎者們列在一起,我的激動之情難以言表。”奇普菲爾德表示:“我把此次獲獎視作一種鼓勵,我將繼續關注建筑的本質和意義,會更加重視建筑師在應對當下氣候變化和社會不平等方面的挑戰中能做出的貢獻。我們深知,身為建筑師需要扮演一個顯著角色,通過不懈地互動互聯,不僅要去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更要去創造一個公平的、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我們必須超越這一挑戰,并幫助和啟發下一代,讓他們有遠見和勇氣來擔當責任。”

莫蘭綜合體, 照片由 Simon Menges 提供
他的建筑職業生涯橫亙四十多年,所完成的一百多個作品紛繁多樣,涵蓋了市政、文化、學術建筑領域,還包括各類住宅和城市總體規劃等,遍及亞洲、歐洲和北美。
2023年度評審辭中提到:“在公共領域,他致力于呈現和定義低調但充滿變革的市政面貌——即使是私人委托,其風格精簡,規避畫蛇添足、遠離潮流時尚,一切都在向當代社會傳遞出最切題的訊息。將淬煉出的設計方案以深思熟慮的方式付諸實施,雖然近年來不那么明顯,這種能力是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維度:可持續性即相關性,它不僅消除了多余的東西,而且是創建物質和文化上都可持久的建筑的第一步。”
奇普菲爾德充分考慮了建筑對環境和歷史的永久性影響,接納現有的一切,在與時間和地點的對話中進行設計和介入,并采用和更新每個地點的當地建筑語言。詹姆斯·西蒙美術館(德國柏林,2018年)位于Kupfergraben運河沿線的一個狹長島嶼上,通過作為博物館島入口的宮殿橋與河岸連接。宏大卻低調的柱廊令人嘆為觀止,將一個露臺、一個寬敞的樓梯和許多開放空間圍攏起來,可以讓充足的光線射入寬闊的建筑入口。其設計讓人們視野開闊,能夠由內至外觀賞到更豐富的景色,甚至看到相鄰的建筑和周圍的城市景觀。
主辦方凱悅基金會主席湯姆士·普利茲克先生表示:“他充滿自信但絕不傲慢,從不跟隨潮流;他直面傳統與創新之間的關聯,并秉持對歷史負責和為人類服務的態度努力加以維護。他的作品優雅而精湛,但他對自己設計成就的度量卻是社會和環境福祉,致力于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

特納當代美術館, 照片由 Simon Menges 提供
在翻新工程中,他精準的設計中充滿了他對歷史敏銳的見解,他始終著眼于挽救原有的設計和結構,而不是完全用現代建筑取代。奇普菲爾德感慨道:“作為一名建筑師,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建筑意義、記憶和遺產的守護者。城市是歷史的記載,而建筑通過歲月的洗禮也會變成歷史記錄。城市是動態的,它們不會在原地靜止,而是不斷地演進。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拆除了一些建筑,并用其它建筑取代它們。因為人們選擇維護自身利益,因此“只保護最好的建筑”的觀念是不夠的,對那些能夠反映城市演變豐富性的特點和特質,還需要考慮對它們進行保護。”
柏林新博物館(德國柏林,2009年)始建于十九世紀中期,在二戰期間被摧毀并荒廢,奇普菲爾德在修復過程中展現出他對保存和重建增建兩者之間的審慎辨析。這是一場新與舊的對話,過去的建筑被放到顯著的位置,從而營造出充滿現代性的場景,例如,一個全新的、非常醒目的主樓梯,兩側的墻壁上顯現出原有壁畫和舊材新用的手法,甚至還帶有被戰爭破壞的痕跡。寬闊的室外空間成為所有人的交流場所——包括那些從未進入過畫廊的人。

胡美茲博物館, 照片由 Simon Menges 提供
評委會主席、2016年普利茲克獎得主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闡述道:“當前,許多建筑師都將客戶委托視為擴展其自身作品集的機會,而他卻用精心挑選的技能、精準的工藝來應對每一個項目。有時需要一種張揚而具有紀念意義的手法,有時又需要他不能留下自己的痕跡。但是,他的建筑將始終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因為他的終極目標是為造福更多人,不追隨潮流反而讓他的作品得以永存。”
舊行政官邸大樓(意大利威尼斯,2022年)的歷史可追溯到十六世紀,他對這座位于市中心的建筑的修復和再造重新界定了它的市政功能,首次對公眾開放。他堅持建筑和工藝水乳交融的理念,通過自己的工作流程升華了兩者間的伙伴關系。傳統工匠復原了原始的壁畫、水磨石和粉彩地面以及石膏裝飾等,揭開了歷史的層層面紗。經過修復的建筑現在可以從上方和內部欣賞到景色,露臺、展覽活動空間、禮堂以及由一系列拱門串聯而成的畫廊空間都一覽無余。
他的每一個作品都成為服務社會的公共事業,例如當初主要作為參賽隊伍和贊助商臨時接待場所的美洲杯大樓(西班牙瓦倫西亞,2006年)。建筑室外空間比室內空間更大,懸挑的觀景臺十分寬敞,分布在每個錯落有致的平臺周邊,有些觀景臺的進深可達15米。奇普菲爾德利用二層的零售商店和無障礙平臺為公眾設置了一個活動場所,在那里可以縱覽運河和城市的美景。通過這一層的一個坡道可直通場地正北側的公園。他對莫蘭綜合體(法國巴黎,2022年)進行了翻新和擴建,涵蓋了高檔住宅和經濟適用房、零售和餐廳場所、酒店和青年旅社、裝置藝術空間和城市屋頂花園,為社區重新注入了活力。建筑師沿著原有建筑的底部設置一系列承重拱廊,將新建體量托起,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聚集空間,吸引人們進入或者穿越這段從莫蘭大道通向塞納河畔的全新視覺通道。

豬名川陵園禮堂和訪客中心, 照片由 Keiko Sasaoka 提供
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建筑,他的作品都為社會賦予了共存和交流的機會,既促進了人們的社會歸屬感又保護了個體獨特性。
愛茉莉太平洋總部(韓國首爾,2017年)就實現了個體與集體、私人與公共、工作與休憩的和諧統一。玻璃幕墻上的垂直鋁板提供遮陽功能,幫助調節溫度和自然通風,并呈現一種半透明感,促進了建筑的使用者、周邊和觀察者之間的和諧關系。公共中庭、博物館、圖書館、禮堂和餐廳等公共設施使得辦公空間得到平衡。中央庭院可讓視野延伸至附近的建筑,而多個空中花園則進一步促使了社區內部與外部元素的互動。
在位于北攝山脈的豬名川陵園禮堂和游客中心(日本兵庫,2017年),在這里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相互融合,兼具獨處和聚會的場所,既可覓得平靜,也可參訪探尋。這些相互聯系的元素,在擁有紅色泥土般質感的整體建筑中得到了體現,室內外的樓梯和小徑順應地勢,營造出連綿不斷的空間體驗,隱蔽的無教派禮堂和游客中心彼此呈對角線排列。
2023年度評審辭中寫道:“在不同的城市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座一眼就認出來的戴衛·奇普菲爾德建筑,而是看到了針對每種不同情況而設計的戴衛·奇普菲爾德建筑。盡管他的每座建筑都彰顯著自己的存在,同時又能與周邊社區建立新的聯系。他的建筑語言既遵從基本設計原則,又能靈活地適應本地文化,實現了真正的平衡……戴衛·奇普菲爾德的作品將歐洲古典主義、英國文化的復雜性,乃至日本的精致風格融為一體,是文化多樣性的結晶。”
奇普菲爾德的重要作品還包括河流與賽艇博物館(英國泰晤士河畔亨利鎮 ,1997年)、美洲杯大樓(西班牙瓦倫西亞,2006年)、英國廣播公司蘇格蘭總部(英國格拉斯哥,2007年)、特納當代美術館(英國馬爾蓋特,2011年)、圣路易斯藝術博物館(美國密蘇里州,2013年)、Joachimstra?e園區(德國柏林,2013年)、胡美茲博物館(墨西哥城,2013)、潘克拉斯廣場辦公樓(英國倫敦,2013年)、西溪天堂·悅莊(中國杭州,2015年)、皇家美術學院總體規劃(英國倫敦,2018年)、霍克斯頓公館(英國倫敦,2018年)、西岸美術館(中國上海,2019年)、蘇黎世美術館(瑞士蘇黎世,2020年)、洛克·外灘源(中國上海,2021年)和陶溪川文化區(中國景德鎮,2022年)。
奇普菲爾德是普利茲克建筑獎的第52位獲獎者。他目前居住在倫敦,并在柏林、米蘭、上海和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開設辦事處。2023年普利茲克獎頒獎典禮將于今年5月在希臘雅典舉行。
評審辭
普利茲克建筑獎是為了表彰其在建筑設計中所反映出的天賦、遠見和責任感,及其通過建筑藝術對人類社會和人居環境所做出的持續和卓著的貢獻。戴衛·奇普菲爾德的職業生涯以持久專注、風格嚴謹和作品的一致性而著稱,獎項宗旨中的兩個核心訴求在他這里實現了無縫地整合與平衡。
基于建筑師本人對這一學科深入和持續地領悟,他對自己在建筑中所追求的目標所做出的回應謹慎、精心、準確而冷靜。這些回應從來都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也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相反,他從始至終關注的是更長遠的目標,對公民和公共利益的不懈追求。

愛茉莉太平洋總部, 照片由 Noshe 提供
戴衛·奇普菲爾德不辱使命,他很好地平衡了每個項目的相關性和地位問題。在實施過程中他謹遵建筑學科的知識和原則,這既需要智慧,也必須謙遜;在特定的項目上如何運用這些知識,需要同時具備才華和經驗。在經手的每個案子中,他都巧妙地選擇了對項目最有幫助的工具,而不是那些可能只會標榜建筑師藝術天分的東西。因此在修復或翻新現有建筑和經典作品的過程中,這位天才建筑師有時幾乎“隱身”了——比如翻新柏林博物館島上的建筑,而對密斯·凡·德·羅標志性的作品柏林新國家美術館的修復則更為甚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接受全新的建筑創作項目時,他可以把廣博的技能表現得淋漓盡致。
他的建筑特點總是優雅的、內斂的,具備永恒感,并輔以干凈利落的結構和精致的細節,每個作品都彰顯出清晰的風格、令人驚喜、蘊含豐富的底蘊并自信地存在著。在這個過度商業化、過度設計和夸張的時代,他始終能實現平衡:無論是在現代極簡主義建筑語言和表達自由之間,抑或在抽象陳述和嚴謹優雅之間——而且從不缺乏復雜性。

舊行政官邸大樓, 照片由 Richard Davies 提供
保持著一絲不茍、始終如一的設計質量,戴衛·奇普菲爾德的作品涉獵廣泛:涵蓋從公共市政和商業建筑,到住宅和零售建筑等各種類型。但從職業生涯的早期起,博物館就一直是他的特別關注點。無論是景區里的小規模獨立作品,還是城市中顯著而又往往復雜而精致的大型紀念物,他的博物館作品向來無視“博物館是精英文化場所”這一觀念。他一次又一次地詮釋了博物館設計的真實要求:不僅要為藝術創造一個展示場所,還要與所在城市交織為一體,打破界限,邀請廣大公眾參與其中。他的博物館建筑一再地創造出新的市政空間、新的城市動線,以及整合城市現有肌理的新路徑。
在奇普菲爾德手中,博物館從建筑學和博物館學的“金絲雀”轉變為能給市民生活帶來改觀的場所。寬闊的室外空間使它們不再是藝術品的堡壘,而是交流、聚會和觀賞的場所,建筑本身也成為送給城市的一份禮物,一個共享之地,即便那些從不進博物館的人也樂在其中。簡言之,他的建筑在看似矛盾的理念之間實現了大局的平衡,既作為建筑設計自身必須是完整的,整體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深思熟慮,同時創造出了與城市和社會的關聯,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地區風貌。

海浦沃斯美術館, 照片由 Iwan Baan 提供
戴衛·奇普菲爾德堅持不懈地追求多樣化、堅實和具備連貫性的作品,他時刻進行著對“本地特色”的嚴肅思考——或稱之為“地方精神”,也就是建筑所在地日益多樣化的文化背景。在不同的城市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座一眼就認出來的戴衛·奇普菲爾德建筑,而是看到了針對每種不同情況而設計的戴衛·奇普菲爾德建筑。盡管他的每個建筑都彰顯著自己的存在,卻能與周邊社區建立新的聯系。他的建筑語言既遵從基本設計原則,又能靈活地適應本地文化,實現了真正的平衡。他將柱廊元素納入到歐洲項目,在中國項目中則融合了庭院元素,他使用當地材料的手法相當高級又巧妙,而在復雜結構中則能運用常規技術。從他的建筑作品中始終流淌出的詩意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量。戴衛·奇普菲爾德的作品將歐洲古典主義、英國文化的復雜性,乃至日本的精致風格融為一體,這是文化多樣性的結晶。
在公共領域,他致力于呈現和定義低調但充滿變革的市政面貌——即使是私人委托,其風格精簡,規避畫蛇添足、遠離潮流時尚,一切都在向當代社會傳遞出最切題的訊息。將淬煉出的設計方案以深思熟慮的方式付諸實施,雖然近年來不那么明顯,這種能力是可持續性的一個重要維度:可持續性即相關性,它不僅消除了多余的東西,而且是創建物質和文化上都可持久的建筑的第一步。

皇家美術學院總體規劃, 照片由 Simon Menges 提供
在體驗戴衛·奇普菲爾德的作品時,人們腦海中浮現出的特質之一往往就是經典,這是一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特質。經典不在于風格,而在于對建筑行為和藝術責任的忠誠,對維特魯威三個基本原則的忠實:堅固、實用和美觀。奇普菲爾德并沒有著眼于創造標志性的、孤芳自賞的建筑表達,而是交替運用內斂和大膽,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方式詮釋著建筑的角色。
戴衛·奇普菲爾德堅信,在地球這個人類家園變得日益脆弱的時代,建筑師的角色就是培育新的方式方法以改善人們的生計和生活。他的愿景已不僅僅是把單個建筑融入其所在地點和文化,而是拓展到對地點和文化更廣泛的定義和理解。
近年來,戴衛·奇普菲爾德履行這一職責的形式不再拘泥于建筑,而是將他有關空間和環境的專業知識用來規劃和保護他的第二故鄉——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亞地區的景觀。在這里,他設立的RIA基金會希望能為保護這個地區相互交織的景觀、土地傳統以及農業和生態出謀劃策,在未來幾十年間幫助保護和拓展生態系統,以應對所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
鑒于戴衛·奇普菲爾德在其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嚴謹、正直和切中肯綮,已經超越了建筑學領域的范疇,彰顯了其對于社會改良和環境改善的執著精神,我們將2023年普利茲克獎授予他。
獲獎者簡介
戴衛·艾倫·奇普菲爾德爵士1953年出生于倫敦,在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的一個鄉村農場長大。大量的谷倉和各種農舍建筑給他帶來的驚嘆充溢在童年回憶中,他對建筑的最初而強烈的實物印象由此形成。
“我認為好的建筑會提供一個環境,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就像所有意義重大的事物一樣,它們既是前景又是背景,而我一向對前景不太感興趣。建筑可以對我們的儀式和日常生活進行強化、支撐和幫助,我最喜歡也是最享受的生活體驗是讓平常的東西變得特別,而不是讓特別的事物成為所有。”
他1976年畢業于金斯頓藝術學院,1980年從倫敦建筑聯盟學院畢業,在那里他學會了如何成為一名具有批判思維的建筑師,學到了如何重新構想每個元素的潛力,從而讓每個項目的意義都超越建造任務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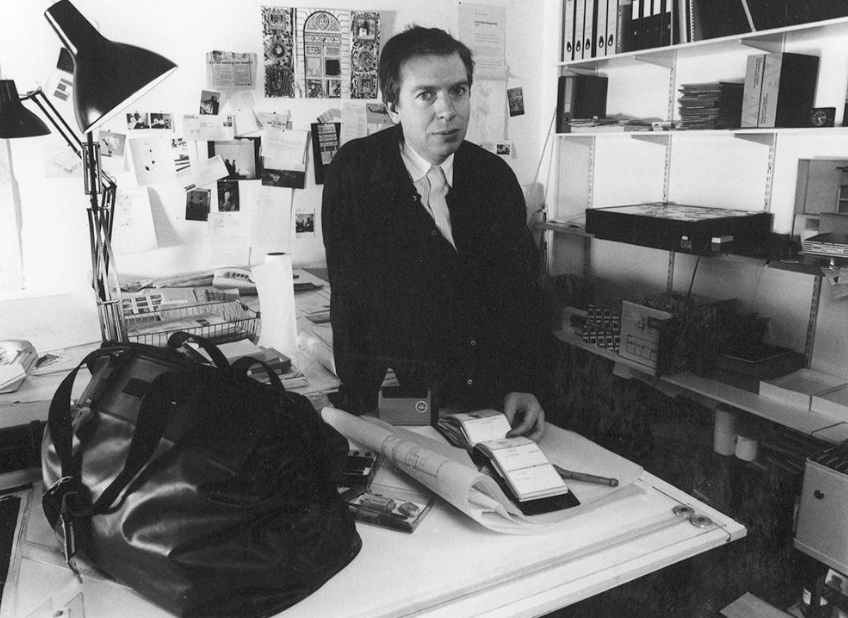
照片由 David Chipperfield 提供
“設計不是用顏色和形狀來堆砌,而是要發展出一系列兼備嚴格性和結果的問題和想法。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你選擇哪條路徑已經不重要了——只要你堅持走下去,并且在過程中取得成果。”
他曾效力于建筑大師道格拉斯·斯蒂芬、1999年度普利茲克獎得主諾曼·福斯特和已故的2007年普利茲克獎得主理查德·羅杰斯。1985年在倫敦成立了戴衛·奇普菲爾德建筑師事務所,后來又在柏林(1998年)、上海(2005年)、米蘭(2006年)和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2022年)設立了辦公室。
他的早期職業生涯始于倫敦斯隆街,為三宅一生的門店做室內裝潢設計,后來在日本從事建筑工作。河流與賽艇博物館(英國泰晤士河畔亨利鎮,1989–1997年)是他在自己故鄉承接的第一個建筑設計項目。此后他繼續在海外從業,早期成功作品包括柏林新博物館(德國柏林,1993-2009年)的重建和再造,以及詹姆斯·西蒙畫廊(德國柏林,1999-2018年)。他把自己高度的責任感歸結于在職業生涯的成形階段,在海外為當地文化建造建筑的經歷。

Joachimstra?e園區, 照片由 Simon Menges 提供
合作一直是他的從業實踐的基礎,他堅信:“事實上,好的建筑來自于好的流程,而好的流程意味著你要與多種力量接觸與合作。”四十年間,他創作了一百多個紛繁多樣的作品,涵蓋了市政、文化、學術建筑領域,還包括各類住宅和城市總體規劃等,遍及亞洲、歐洲和北美。

柏林新博物館,照片由 Ute Zscharnt 為戴衛·奇普菲爾德建筑事務所提供
隨著他的建筑實踐變得越來越豐富,他對社會和環境福祉的倡導也越來越鮮明,他譴責那些不為當地社會服務,而臣服于全球經濟大鱷的建筑商品化行為,譴責就此形成缺乏永久性的意識,導致氣候危機。“建筑師不能置身事外,需要與社會同行。誠然,我們或許可以挑釁和抱怨,我們也能夠找到可茲效法的東西。但我們首先需要一個規劃框架,既要有雄心壯志,也要有優先次序。從本質上講,我們現在不得不期盼,環境危機能讓我們重新思考社會事務的優先順序——追逐利潤并不應該成為激發我們做出決策的唯一動因。”
近年來,他對加利西亞社區賦予厚愛,奉獻熱情。加利西亞是西班牙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但這里卻以高品質的生活而著稱。2017年,奇普菲爾德成立了RIA基金會,贊助相關研究和理念推廣,協調規劃未來的發展,沿著阿勞薩灣的海岸線推動以當地為核心的自然和建筑環境保護,籍此應對全球挑戰。

舊行政官邸大樓, 照片由 Alessandra Chemollo 提供
奇普菲爾德曾獲得英國皇家建筑學會金獎(英國,2011年)、歐盟當代建筑獎——密斯·凡·德·羅獎(西班牙,2011年)以及海因里希·特森諾獎(德國,1999年)等獎項。他曾入選皇家美術學院院士(2008年),被授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功績勛章(2009年),被日本藝術協會授予日本皇室世界文化(建筑)獎(2013年),他是英國皇家建筑師學會成員,也是美國建筑師學會和德國建筑師學會的榮譽會士。
2012年,奇普菲爾德主持策劃了以“共同基礎”為主題的第十三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2016年至2017年被選為勞力士創藝推薦資助計劃的建筑學導師;并于2020年擔任Domus的特邀主編;他曾于1995年至2001年在斯圖加特國立美術學院建筑系擔任教授;2011年在耶魯大學擔任建筑設計專業“諾曼·R·福斯特”客座教授。
他于2004年被授予大英帝國司令勛章(CBE),2010年被封為爵士,并被授予名譽勛位。
專欄編輯|Yihan
發文編輯|Shixin
審核編輯|Zyi
版權?建道筑格ArchiDogs,轉載請聯系media@archidogs.com
若有涉及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系media@archidogs.com,我們將盡快妥善處理。
來源普利茲克官網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