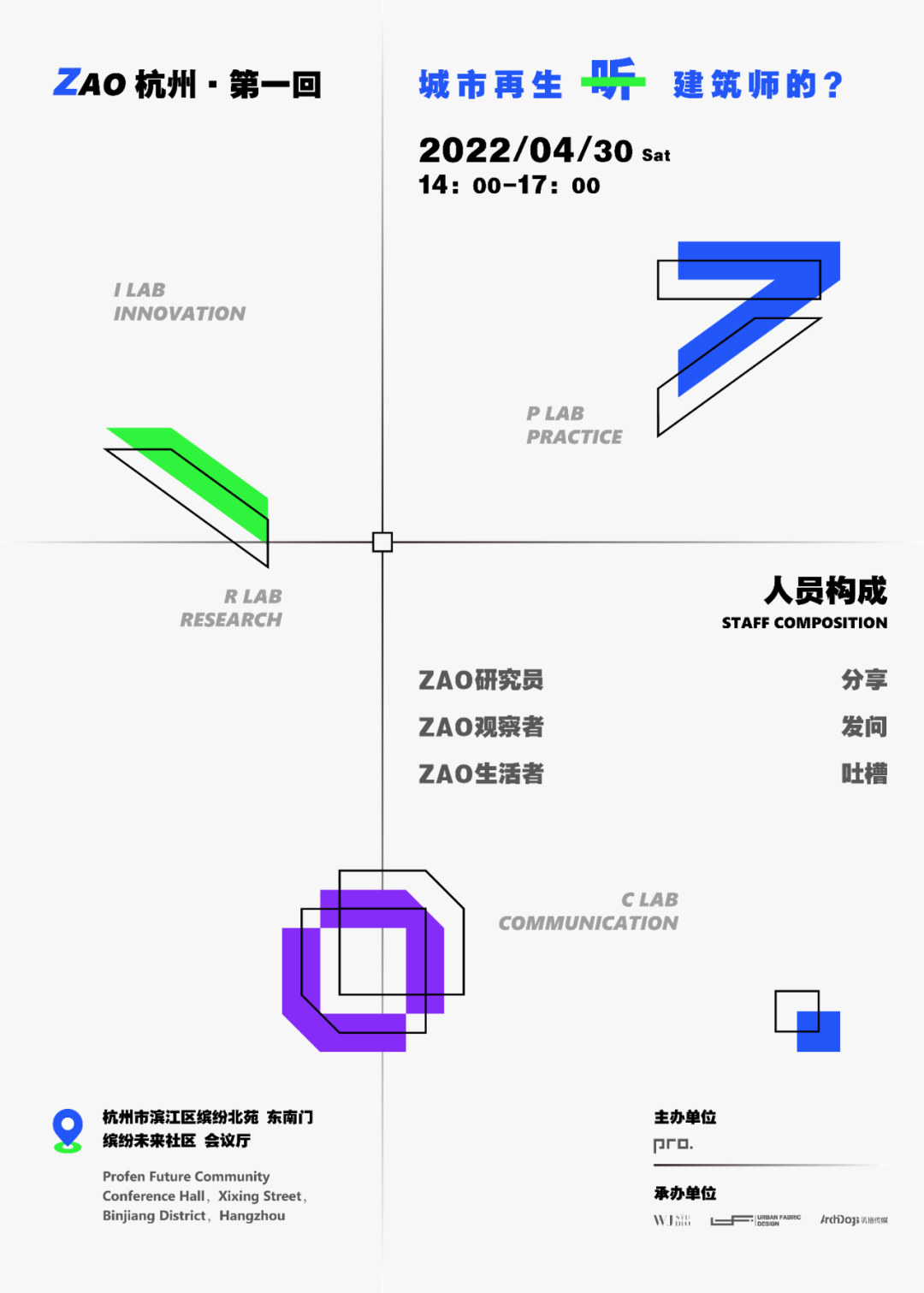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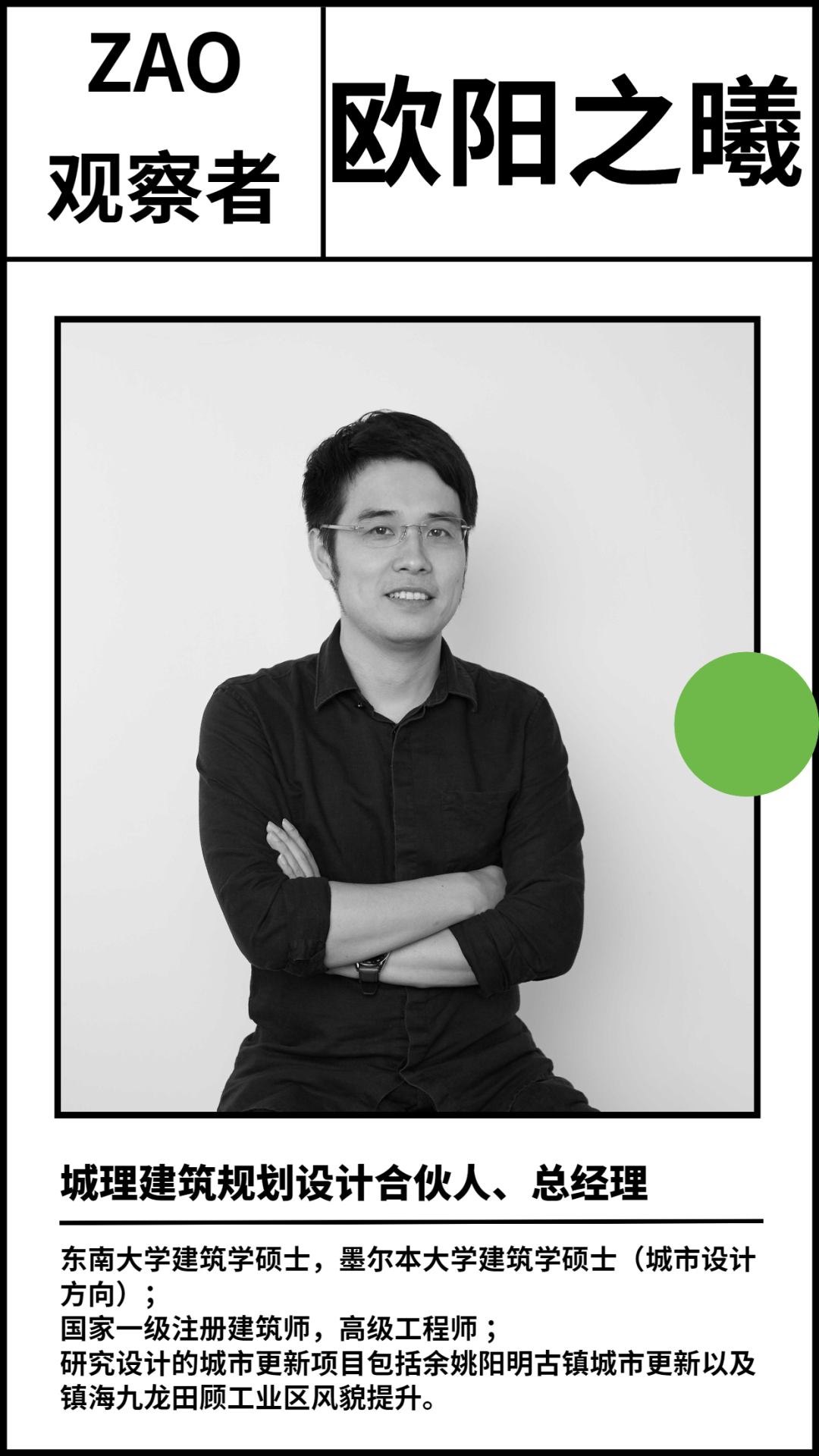


歐陽之曦
合伙人總經理
東南大學建筑學碩士
墨爾本大學建筑學碩士(城市設計方向)
東南大學建筑學博士畢業
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高級工程師

肖杰
合伙人 副總經理
福州大學建筑學學士
█ 記錄建筑作品的方式有照片、文章、短視頻等多種方式,為什么會選擇采用比較辛苦的紀錄片形式呢?
A: 我覺得其實建筑影像這種描述建筑作品的形式現在已經特別多了,很多設計師都在靜態的照片之外,希望用移動的鏡頭來讓大家感知自己的作品。但我認為這個就像看櫥窗,你是隔著一個玻璃來觀察商品的,你也不知道這個商品的成分和工藝。
建筑首先是一種工程,它是有制作或者建造的過程的,但它又不是那種流水線產品,千篇一律,它是有唯一性的。所以我覺得記錄下建筑作品從無到有的誕生過程,可能也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如果《舌尖上的中國》只是把那些菜肴的成品拍攝給你看,你也不一定有食欲,但是它把食材的甄選、制作乃至這個菜肴背后的人文都一起展示給你之后,你對這個菜肴就會有更多層次的感受和理解。
這就是一種紀錄片,不是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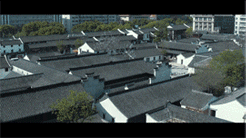

█ 紀錄片要求拍攝的時候要完全真實,用豐富的素材串聯故事,這個片子是怎么做的?
A: 是的,其實我們就是想把建筑師的工作和思考真實地呈現給大家。建筑設計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工作,從場地調研到方案設計到施工圖,再到跑現場,需要處理非常多的問題。我覺得現在很多媒體宣傳甚至是建筑師自我的描述,都在把大家對建筑師這個職業的認識往一個很不對頭的方向去引導。
我曾經開玩笑說,很多建筑師都在給自己分類下定義,總計三個類別:詩人、藝術家、哲學家,然后就開始角色扮演。其實事實根本不是這樣的,有時候我的一些朋友,不是我們這行的,會說歐陽你一點都不像建筑師,我說為什么,他們說因為你不是很酷。
所以我覺得大眾因為媒體的引導,對建筑師的工作屬性是有很大的誤解的。
這個紀錄片就是去真實呈現建筑師的工作,我們希望通過翔實的記錄,把點點滴滴都記錄下來。


█ 與我們平常看到建筑建成影像不同,這個影片自始自終都特別有煙火氣、接地氣,你是怎么去思考這個方面的?
A: 回到剛才那個問題,建筑影像的真實性在哪里?建筑是要被使用的,沒有人的建筑不是真實的。
我最近看到有些建筑影像拍的和世界末日一樣,因為鏡頭里一直沒有人。有兩個國外的建筑紀錄片我印象很深,一個是說福斯特事務所在倫敦的黃瓜樓是如何設計建造的,一個是YouTube上一個講訴一個普通工人購買一處荒廢古堡進行改建的。這兩部紀錄片都非常坦然地展現了建筑設計的周折或者是建造工作的艱辛,影片中只是在最后把建筑完成后的狀態比較唯美地展現了十幾秒鐘,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說博弈和協調。我覺得這種真實非常寶貴,我覺得看完黃瓜樓的建造過程,我才第一次對福斯特事務所的工作切實地欽佩,建筑師需要在不斷的否定和挫折中去嘗試下一種解決方案,然后在復雜的建造過程中堅守工地,解決更加困難的工地問題。紀錄片完全沒有去突出福斯特爵士的偉岸或者說其他設計師的風度翩翩,在片中大部分時候他們都愁眉緊鎖,不停的溝通,制作模型,做測試實驗。這種緊張感一直到片尾才緩緩地釋放掉。
建筑師在建筑的生產中是一個重要參與者,但并不是唯一的角色,你還需要使用者,反饋者,評論者。建筑是一種社會性產品,不是一個安靜的雕塑。


█ 在影片中,原住民對你們的探訪抵觸嗎?他們對于這個項目有什么看法?
A: 原住民對于我們設計的幫助是巨大的。沒有他們,甚至都無法還原我們負責的西片區的歷史原貌特征。因為這個街區在幾十年的歷史中改建擴建,乃至亂搭亂建很嚴重。因為一些特殊的歷史原因,很多房子的主人都變了,他們對這些原本不屬于自己的房子更加的不愛惜,所以很多院落廊道都被掩蓋住了。
西片區中一直留守的周氏家族,是現存的對這個街區最為了解的人,周炳銓老人四歲就生活在這里,他們家的宅第是文物保護單位,建于1934年,也就是說他親身目睹了80年來這個街區的變遷,每戶人家的姓名職業甚至是家族的歷史他都說得出來,哪些房子被日軍炸毀了,哪些是70年代修建的公房,哪些房子拆了又建,這些東西他和他的老伴都是如數家珍。這些口頭文獻是我們能獲得的最珍貴的資料,從整體上支撐了我們設計師對于這個片區的總圖的判斷和布局。原住民的態度開始是不配合的,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生活遭到了侵擾,而且擔心自己的宅子被拆除。其實建設單位對他們很友好,也沒有去亂拆。最后項目開街的那天,幾位至今還生活在這個街區里的原住民非常愉快地逛了一上午,他們覺得自己的家周邊環境提升了,更加熱鬧了,沒有了亂七八糟的破敗感,但是很多老記憶和老物件還在。所以他們態度的轉變很明顯,我們在影片中也很忠實地記錄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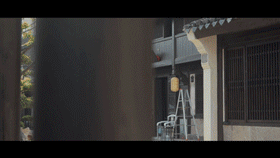
█ 你們的影片視角和呈現方式非常獨特,不僅描述了建筑師的工作和作品,也探討了很多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問題,今后你們還會做這類建筑作品的紀錄片嗎?
A: 城市舊區改造更新這個領域,本身就是話題性和矛盾性很強的。所以拍攝這類題材,你想去搞個唯美默片,幾乎不可能。我們去制作這種紀錄片,很看重建筑作品或者事件的一種復雜性,紀錄片影像可以幫助大家去理解一件比較復雜的事情,會有一種開放的態度和視角,是有批判性的,不會有唯一或者肯定的答案。
今后如果有機會,我們會很謹慎地選擇拍攝的題材,可能也會去拍那種比較獨立的小建筑作品,哪怕是商業性質的。因為還是那句話,你觀察記錄的角度不同,呈現的方式就不同,知行合一。
其實我覺得這些拍攝角度或者拍攝的思路可以反映建筑師的一些他自己對于設計的價值觀。即使我們去拍攝今后一些設計形式感很強的作品,我們也不會去拍那種鏡頭里一個人都沒有的世界末日型場景,因為我不是藝術家,我是建筑師,我看到的世界是豐富和喧囂的。

█ 拍攝過程中,你們和影像公司是如何溝通的,他們如何看待這個復雜且艱辛的任務?
A: 單幀映畫是一個年輕的但是很有想法和創作能力的影像設計機構,我覺得他們接了這個單子估計一直挺后悔,因為太難拍了。最后這些素材的整理,以及敘述事情的方式也和平常的影片不太一樣,但他們真的堅持下來了,影片剪輯的打磨,鏡頭的選擇,文字的描述,反反復復修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我是一直和他們在一起去討論這個影片的拍攝想法,一起去編寫修改腳本。我鼓勵他們大膽地去嘗試一些鏡頭和敘事手法,我自己就是個性格比較鮮明的人,所以我也不喜歡那種四平八穩的節奏。一個影片需要有沖突,沖突和矛盾是真實的,如果一個舊城改造拍的無比浪漫,我覺得無論是制片方還是拍攝方都是偏離了真實。攝制組來來去去現場走了十幾次,最后開街前夜也和我蹲守在現場,他們最后基本也快成這個項目的百事通了。
影片殺青后,他們也很開心,覺得我是個挺兇挺嚴格,但是卻愿意放手讓他們去創作的客戶,能夠接受很多別的客戶不能接受的想法和場景鏡頭。我很感謝他們這兩年來的付出。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 城理設計
版權?建道筑格ArchiDogs,轉載請聯系media@archidogs.com
若有涉及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系media@archidogs.com,我們將盡快妥善處理。
 "/>
"/>
 "/>
"/>
